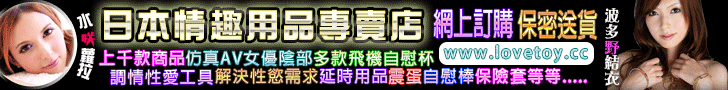强烈的灯光照在铺著绿绒的桌上,不远处吃角子老虎叮叮咚咚地吐著硬币,骰子桌上不时传来欢呼声,四周人来人往,嘈杂不堪。这些,对我都没有影响,我只是全神贯注在牌上。在我面前的桌上,排列成堆红绿混杂的筹码。靠近庄家的红黑圈子里,摆著二十元的筹码,和两张方块。十一点。庄家朝向我,左手牌盒里的牌呼之欲出。我加上四个红筹码在圈里――十一点当然是赌倍罗。庄家给了我一张牌,九点。还不错。庄家发完下手的牌,一家爆掉,两家停住。庄家翻开牌,一张九点,加上十点,正好十九点。他赔给我八个红筹码,收走牌,把其他人筹码一扫而空,然后开始洗牌。我这才放松下来,伸伸懒腰,看看周遭。
这里就是拉斯维加斯,世界最大的赌城。一个纸醉金迷的罪恶渊薮,一个让人美梦成真的幸运之都,或是一个轻松解忧的娱乐中心,这端赖一个人看事情的角度了。我想大部份人到这里来不过要轻松轻松,享受一下赌博的乐趣,运气好赢了钱固然可喜,运气不好赔上几文也无伤大雅。真正的赌棍赌徒那是少之又少。我呢?我当然也不是赌棍。只不过一年前在 Internet 上到处乱逛,很“凑巧”地找到一个黑杰克的模拟程式,从它的注解中发现它用一套奇怪的押注法,可以赢多输少。我本来不相信,但在我自己重写模拟程式,并且换过十数种乱数产生器后,我大致相信了。这次来拉斯维加斯参加电脑展,正好趁机验证一番。
黑杰克,也就是二十一点,是比较公平的赌局:一般公认庄家,也就是赌场,只比赌客多零点三到零点八个百分点的优势。像轮盘,赌场有五点三个百分点的优势。吃角子老虎更不值一提了,赌场要怎么操纵吐钱的比例都可以。但是吃角子老虎还是赌场里最多顾客的地方,尽是些头发花白的老先生老太太们。他们总是换了整盆的硬币,守在嗡嗡轻哼的转轮前,一个银币接著一个银币地投著。赢钱也好,输钱也好,似乎都和他们无关。来这儿只不过是来打发儿女远离、孤单寂寞的残年。
我将筹码留在桌边,请庄家看著,到洗手间解放一下。回来时庄家已经洗好四副牌,重新开始另一轮黑杰克了。很显然我的秘诀十分有效,已经帮我赢了好几百块,早就把老本收回口袋里。既然赌的是赢来的钱,我更加大下注的额度――输也是输赌场的钱,怕什么呢?这么一来,我面前筹码累积的速度更快了。
我转头四望看看同桌的赌客,他们并没多大起色。我移目梭巡,目光最后落在一个女孩身上。她在我左手边第二位,隔著一个老太太。她也是东方人,一头乌亮垂肩的长发,配著一副纤细的身躯,是个非常俏丽的女孩。我之所以注意到她,与其说是由於她的俏丽,不如说是她的年纪。她看起来是这么年轻,我甚至怀疑她是否满了可以赌博的法定年龄。这疑问只维持了一会儿就消失了――庄家想必已经查过了她的驾照,要不然他不会让她上桌的。不论如何,她在输钱,输得还不少。很显然她根本不懂黑杰克的诀窍,搞不好这是她第一次玩黑杰克。出於一片好心,我开始给她一点建议。由於我是这桌上的大赢家,她也接受这些建议,一连赢了好几把。
再赌一会儿,我觉得已经有点累,心想见好就收,离开赌台,到出纳柜台兑换筹码,数一数,有两千多块钱。在吧台边找到一个位置。酒保走过来。
「马丁尼。」简单、清爽,一向就是我的选择。人世已经够复杂了,不必连喝杯酒轻松一下都要讲究。
我在赌桌上是从不喝酒的,只有在赌完后才会喝上两杯。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别以为赌桌上源源不绝免费提供的啤酒和鸡尾酒只是赌场招待客人的一套,那是有目的的。酒精会影响判断力,三杯下肚,任你再会算都没有用。
有一人在我旁边的位子坐下。
「嗨!」
原来是同桌的女孩。她清脆的声音,似乎掩过了赌场里嘈杂模糊的人声。
「Hello!」我有点惊讶。
「谢谢你刚刚的指点。」
「不必客气,我乐意效劳。能让我请你喝杯酒吗?」
「谢谢,不过我不喝酒!」
「来杯可乐好了。」
「好呀!」
我示意酒保给她一杯可乐。
「这是你第一次来拉斯维加斯?」我没话找话地道。
「嗯,你怎么知道?」她问。
谁都知道,看你一副天真无邪的模样。
「我看你好像不太会玩黑杰克。我猜想你大概是第一次。」
「嗯,不但如此,我的运气坏透了!」她懊恼的说。
听她的口音好像不是 native。问问看吧。
「你从那里来?」
「旧金山。」Bingo!
「真的呀!我住在南湾。你是中国人吗?」
「嗯。我在台湾长大的。你也是台湾来的吧?我们可以说中文罗。」太好了!这样沟通起来就没有任何问题了。你知道的,不是英文沟通有多难,只是和她交谈时,中文似乎是个较好的工具。
「好呀!我是罗杰。你是…?」
「珍妮佛。」
知道名字就不算陌生人了。我们天南地北地聊了起来,从台湾的小吃,科罗拉多的滑雪场,到最近旧金山的歌剧。起先她还有点腆腼,不多时也就和熟识的朋友一样了。她告诉我她是高中时来美的小留学生,刚刚大学毕业,第一份工作就是电脑公司的buyer。这次是跟著老板来见识一下这最大的电脑展。她的老板有事先回去,叫她多待几天看看新产品。但是她太无聊了,就跑来赌场试试手气,不料却大输特输。
看著她这副楚楚可怜的神情,任谁都於心不忍,我跟女侍要了一副牌,就一步步地教起她来。等到她比较熟练时,看看时间,竟然不知不觉已经过了好几小时。时近午夜,正逢晚场秀刚散场,一群群红男绿女迫不及待地加入赌台旁全神贯注地厮杀中的赌客。赌台上阵阵的吆喝声,更让人心旷神驰。
「珍妮佛,你要不要再试试手气?」我问道。
仍然是一副娇憨的表情,「好呀,但是你要看著我哟!」
「Sure!」
我们挤进一张黑杰克的台子,小玩一番。我并没有专心在我自己的牌上,而是如我承诺的,时时点醒她。再玩了一会儿,我发现自己连她的牌都没在看,目光不时游移在珍妮佛身上。她的侧面,正是最好的欣赏角度。她长长的秀发如瀑布般倾披下来直到肩膀。挺秀的鼻梁,衬著微弯的小嘴,及因专心而皱著的淡淡蛾眉。
「我一定要把到你…」,我告诉自己。
她注意到我的目光,转过头来对我嫣然一笑。我报以鼓励的笑容。低头数数桌上的筹码,发现她已经赢了不少,我自己却小赔。看看时间,已经快一点钟了。虽然珍妮佛的兴致还很好,但她也显得有点累。我提议送她回去休息时,她还有点舍不得目前的好运。当我再三保证我的方法和运气无关,并且答应明天要陪她去所有的大赌场绕一圈――她还没去过其它赌场呢!――她才跟我出了大门,漫步向Luxor走去。
她的公司真凯!Luxor是最新开幕的赌场旅馆,金字塔型的黑色建筑,大门入口就在一尊硕大狮身人面像的腹部。整个装潢都是古埃及式,住一晚总得要一百多块钱。这才是人住的,哪像我们公司,每次总将我们塞入一些小汽车旅馆,就为了省那一点钱。
挤过人潮汹涌的大厅,在埃及法老的头像下,她停住了,,转过身来。脸上一副似笑非笑的表情。
「谢谢你送我回来。明天什么时候见?」
「早上九点钟,在这儿见。」
「好啊,晚安。」
「晚安。」
看她往电梯方向走去,我也转身出了Luxor的大门。回到我下榻的旅馆,冲了一个澡,边想著明天的行程,边钻入被中。不知什么时候沉沉入睡,也不记得珍妮佛是否出现在梦中?
七点半钟,morning call 准时响起。起床冲澡后,我特意修饰了一番,穿上行囊中最 casual 的一套衣服,出了旅馆,向Luxor慢慢踱去。
我走进大厅,她已经在那儿等著了。我连忙看看时间,还好,我没有迟到,是她早到了。我纳闷著,这代表什么呢?是不是她也很期待这个约会?
我来不及想得太多,因为她已经走了过来,边微笑著边对我打招呼。我上下打量著她,已经是和昨晚的打扮完全不同了。昨天白衬衫加蓝牛仔裤的打扮,虽然衬托出她清丽的外形,未免有点过於小家碧玉的味道了。今天她换上了一套淡绿色的连身套装,搭配了一件白色的外套,飘飘逸逸地走来时,我看得呆住了。她走到我身旁,看我仍然目不转睛地注视著她,轻轻一笑,伸出手来。
「Shall we?」
我如大梦方醒。
「Oh! Yes,…你…我们…今天…」
该死,我今天是怎么了?别搞砸了!
我连忙伸出我的手臂,她大大方方地揽住我的臂弯,转向出口。
就如我所答应的,我带她慢慢地逛著The Strip上的几家大赌场。拉斯维加斯这地方就是这样,每家赌场都有它自己的特色。Excalibur,MGM,…每一家莫不装潢得富丽堂皇,再加上一些特别的主题,或是亚瑟王的中古时代,或是童话里的OZ王国,甚或是小说里的金银宝岛;总之就是要营造出给顾客的一个梦境,他们才会停留,才会大把大把地花钱。
当然,我们也随处试试赌运。或许不该说是赌运,应该说是验证一下我的秘诀。结果自然是不负所望,大大地赢了几笔。随著囊中的钱越来越多,珍妮佛的兴致也越来越高,我不得不阻止她太过招摇。谁知道这些赌场跟黑社会的关系是怎么样?
中午就在一家赌场吃buffet。在赌城这种餐点是出名地□盛,各种口味,应有尽有。我告诉珍妮佛,这儿甚至在用餐时都能赌。为了证明,我买了四张Keno的彩券,边吃边对奖。一顿饭下来就输了廿元。
吃完午饭,出到路上,听得旁边传来一阵结婚进行曲的音乐声。是一个专办快速结婚的地方,也算是赌城的一个特色。看到珍妮佛好奇的神情,我就带著她进去参观。里头的布置就像一个小教堂,数排长椅,稀稀落落地坐著两三人。正好,有一对新人在行礼。他们穿著牛仔裤,只有新娘头上戴著一副头纱。证婚人念完证词,新人交换戒指、拥吻,人生这么重要的大事就这样完成了。
珍妮佛拊耳过来,「好草率哦!真为那个新娘可惜。」
「还可以啦,很方便嘛!」
她白了我一眼,…男人真没情调…,一定是这么想。
「我们就在这儿结个婚,你看怎么样?」
这种玩笑的结果当然是挨上一记粉拳了。我不甘示弱,抓住她的手臂不放。两个人在后面笑著、纠缠著,引得旁边的助手向我们瞪目而视,才匆匆离开。
晃呀晃地,来到Treasure Island的前面,人群聚集,显然有精采的节目。看看时间,正好是海盗船表演登场了。我们挤在人群中,挨挨擦擦,就想找个好位子来看表演。好不容易站定,音乐响起,海盗出场了,快乐地装戴著掳掠来的财富。这时从另一面的水道驶来另一艘船,旗帜飞扬,原来是英国皇家海军的舰只,马上和海盗船展开一场激战。只听得炮声隆隆,火花四射,海盗和士兵纷纷落水,爆炸的热气直扑到我们脸上。海盗自然不敌军舰,眼见就要被消灭了,不料船长放出最后一炮,恰好命中英舰。一阵大爆炸,英舰向左舷倾斜,带著官兵,急速地沉入水中。观众纷纷对海盗报以热烈掌声后四散而去。不到一分钟后,沉没的英舰又缓缓浮起,恢复正常,沿著水道退回出场前的位置,开始为下一场表演做准备。这种机械和特技演员的结合的确是精采绝伦,莫怪这个表演深受游客、特别是小孩子的欢迎。
整个表演过程中,我和珍妮佛缩在一个角落。人实在太多了,我们几乎都无法动弹,肩并肩地看完这场表演。人群稍散,我转头看看珍妮佛,只见她专注地望著英军旗帜冉冉从水中升起,长发披在一边,露出一截雪白的颈子,那娇艳的模样,真让我看呆了。我低下头,闻闻她的秀发,半吻半嗅地溱在她的后颈。大概是弄痒她了,她一边闪躲著,一边笑著将我推开。我心中一荡,就想把她抱住。转念一想,不妥!大庭广众之下,我们又还没到那种程度,万一她抗拒的话,不但场面尴尬,更是前功尽弃。还是稳扎稳打吧!找间气氛好一点的餐厅用餐,再看个晚场秀,看看情况再说。
在Treasure Island里逛了一下,来到两张大海报前,正是晚场秀的海报。这儿是Mystic,在Mirage则是白老虎和魔术。看著Mystic海报上的半裸男体,我决定这个秀应该比较适合。白老虎的秀太家庭化了,看完后还有什么搞头?反正我是导游,珍妮佛都没有意见的。我到柜台买了两张票。看看时间还早,正好先吃顿晚餐。带著珍妮佛来到一旁的Mirage,这儿有一家法式餐厅还不错。进去点了海鲜的开胃菜、主食,再加上一瓶白酒。两人对坐在摇曳的烛光下,醇酒美食,伴随著的是乐队的抒情乐曲。这样的情境,这样的气氛,有那个女孩子不会被打动?
轻轻地说著一些连我自己也不知从那里冒出来的话语,看著珍妮佛在烛光下因著酒精泛红的脸颊,我知道我醉了。醉在这个烛光下,醉在这个笑靥中。俪人相对,又有谁愿意清醒过来?我伸出手去,隔著桌子,覆盖在她的手背上。轻轻抚摸,细细品味著她的肌理。她没有抗拒,翻过手来,握住了我的手。我凝视著她的脸,目光交会在一起,那里面没有羞涩,没有矜持,只有浪潮般的热情。
「叮…。」
我转头一看,原来是隔壁桌的客人正在一齐轻敲酒杯,大概在庆祝些什么。看看时间,也差不多了。挽著珍妮佛离开餐厅,步向Treasure Island,赶赴著Mystic的开场。
带位的侍者,挟著我给的一张五元钞票,将我们带到了靠中间的一个包厢座。点了两杯鸡尾酒,不久灯光也暗了下来。忽然一阵急急的鼓声,舞台上的灯光再现时,已有数名全裸的舞者在台上起舞。不对,不是全裸。他们都著著几不蔽体的短裤,只是全身涂满了灰白的颜料,分不出那里是衣物,那里是肉体。这些舞者身材健美,肌肉纠结,配合著鼓声韵律,舞著高难度的动作。说他们是舞者吧,他们又在展现著只有体操选手才可能完成的动作。说他们在做体操吧,却又那么配合韵律,又那么具有美感。低沉的鼓声,回响在这个剧场封闭的空间里。狂野的节奏,从欲望的深处涌起,一步步地攀上高峰。这那是现代拉斯维加斯的表演?这明明是远古民族祈求丰年,充满肉欲的原始祭礼。
我只觉得口干舌燥,强抑住自己,几乎透不过气来。侧头看看珍妮佛,红晕泛上脸颊,酥胸微微起伏,显然也感受到了这个气氛。我伸出右手,环住她的腰,轻轻地将她拉过来,她的头很自然地靠在我肩上。我的右手在她腰际微微地施加压力,侧过头去,嗅著她的发香,嘴唇轻触著她的耳垂,缓缓地吹著气。在昏暗中,我仍可以看到她的整个耳朵都红了,只觉得她的身体在颤抖著。我大胆地伸出左手,放在她的腿上,慢慢地抚揉著她富含弹性的肌肉。她颤抖得更厉害了,整个人几乎都瘫在我身上。我将她的下巴抬起,低下头,重重地吻在她如花瓣般盛开的双唇上。黑暗里,音乐继续著,一下接著一下――是鼓声,还是我们的心跳?
表演继续著,一支舞比一支舞更狂野,一支舞比一支舞更剧烈。鼓声响起…灯光闪动…阵阵的浪潮…炽热的呼息…无止的冲击…狂乱的探索…愈急愈促…。
砰然一响,一切回复平静。
灯光再度亮起,演员出场谢幕。看看自己,却仍和珍妮佛纠缠在一起,她几乎是整个人坐在我身上。我们赶紧分开,偷偷四下张望,看看是否有人注意到我们。我们后方一桌上的两对夫妇,正在热烈地鼓掌,看到我们,还捉狭似地眨了眨眼睛。Damn!我们的热情演出,大概都落在他们眼中了。我们面红耳赤,忙不咫地离开。
出了大门,混入外头的人群中,沙漠夜晚的低温迎面袭来,脸上的热度才稍稍消退。看看珍妮佛,她脸上仍是红晕未消;看到我注视著她,她不好意思地啐了我一口,头转过一旁,手仍紧抓住我的手不放。成了!现在只是上那儿去的问题而已。
我牵著她的手,沿著The Strip慢慢地往我旅馆的方向走去。经过了Caesar和Dune几家大赌场,她也没有要想进去看看的意思。两个人就这样无言地在人群中漫步著。
走著走著,经过了Luxor前面。一阵寒风袭来,她单薄的外套似乎挡不住,我只觉她一阵颤抖。
「冷吗?要不要加一件衣服?」
其实我巴不得她一件都不要穿。
「嗯。我想上去换件外套。等我一下。」
她拉著我穿过大厅,来到电梯口,却没有要我停下的意思。我只是凝视著她。进了电梯,她按下钮,当电梯开始上升时,一股力量将我推向她。她没有闪避,只是把我抱住。
「怎么回事?」我惊讶地问。
「噢,这个电梯是斜斜上升的。」
出了电梯,磨磨□□地进了她的房间,我将门用脚带上,抓住她的双手,将她整个身体抵在进门的墙上,看著她娇喘细细起伏不已的酥胸,微启期待的樱唇,和热情深邃的双眸,我将头慢慢地低下去。
那感觉仍然是这么强烈,这么炽热。
嘴唇嬉戏著,挑逗著,探索著。身体一寸寸地逼近,一分分地压迫著。胸膛紧顶著坚挺的峰点,磨擦著,弹荡著。我最喜欢这种感觉了。紧紧地抓著她的双手贴在墙上。这是主宰…控制…力量。一股欲望自根处涌起,硬挺挺地亘在我们之间。厮摩著,探索著,梭巡在发梢耳际。我放掉紧抓住她的手,开始探索她的每一曲线,每一幽谷。
她的洋装,不知什么时候已经褪到胸际来了;我并不记得动手解开过拉炼。不管如何,呈现在我眼前的,是白色丝缎下的玲珑峰峦。我的双手轻轻地覆盖上去,掌沿圈住了隆起的周圆,掌心缓缓地画著圆弧,抚揉她峰顶的尖处。一阵颤抖,从她腹部传来的是有如电流通过般的痉挛,振荡著我的坚硬。止不住呻吟,我拉开了丝缎的障碍,暴露出白晰坚挺的乳房,低头含住了一边怒张突挺的粉红顶点,让舌头的动作折磨著她的呻吟蠕动。
她的手滑下去,一边来回地磨擦著我的下腹,一边急急地解著我的皮带。她将我解放出来,继续搓著、揉著,让我更形怒张高挺。我呻吟出声,将她的洋装完全褪下。一副匀称的胴体,我的手沿著浑圆的曲线,一路滑下去,直到她小而坚实的臀部,将她整个人抱了起来。她好轻!像是抱著一个洋娃娃。她纤细的双腿,圈在我的腰际。我用怒张的直竖,顶住了湿润的丝绸,一摩一擦之间,只剩下喘息呻吟的一点力量。
我举步维艰,辛苦地一步步走向床边。不是她的重量,也不是昏暗的光线,只是因为我越陷越深。虽然隔著一层丝绸,我仍能感觉到,随著迈出的每一步,我一点一点地陷入了两道火壁之中。那是什么样的感觉?没有直接接触的那种湿滑,但那热度…那磨擦…。她忽然一阵痉挛,肌肉无法控制地颤动著,手指深深地陷入我的肩膀,仰著头,无声地抽搐著…,她这么快就…?噢!那双壁的动作,那肌肉!…噢!
我重重地倒在床上,只来得及避免压得她太用力。我们仍然联在一起。她紧闭著双眼,臀部仍然在晃动著,我几乎要受不了了。身陷重围,被湿透的绸布厮磨得濒临爆炸,还有什么好等待的?我轻轻抽出,将绸布拨开一旁,微微露出那折磨我的双壁,握住自己,缓缓地逼近…。
她突然用力推开我。我愣住了。怎么搞的?我做错了什么吗?
「对不起…,我不能…。」
WHAT?!
「我今天不安全…,我不想怀孕…。」
…那你刚刚在干什么?搞得我现在吊在半空中!
「我了解。」
除此之外,我还能说什么呢?
「你有没有…保险套?」
该死!在这个节骨眼上才冒出这个问题。但我也不是那么自私的男人,还是得尊重女伴的意愿,尤其在这种事情上。保险套我倒是有,不过是在我的行李里,谁会想到我们会到她的房间,我本来是计划在我房间的…。这时候又怎么可能回去旅馆再来呢?看来只有就近设法了。
「好吧!但我身上没有。等我十分钟,我出去一下!」
我匆匆忙忙著装,等自己稍稍消退,调整一下衣服掩盖窘态。在她的脸颊上亲了一下,冲出房间,全速奔到电梯边,正好有部电梯下楼。心里只想著到那里去弄保险套?
有了!像Luxor这种大旅馆都有一些卖书报的小摊,通常它也会兼卖一些零食和急救药品,也一定有保险套了。到了底层,冲出电梯,向一个女侍问了去处。还好,不太难找,就在附近。我冲了进去,抓了盒半打装的――应该够吧?如果一晚上全用完的话,我恐怕就在床上挂了。付完钱,将店员闪烁的目光抛在脑后,兴冲冲的赶到电梯旁…。
我突然呆住了。她的房间是在几楼几号?我没有半点印象!刚刚上楼时是珍妮佛按的电梯,我没注意是几楼。出了电梯后记得是向左转,糊里糊涂的就进了房间,连房号也没注意…更糟糕的是,电梯口的警卫要看我的房
最受欢迎标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