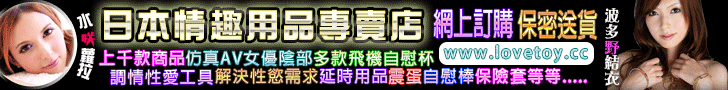第一回入洞房张霞思往事娶新妇林冲展神威 且说北宋朝徽宗十年,虽北有强辽虎视眈眈,西有西夏、吐蕃窥视中原,然东京开封府仍是一片歌舞升平。 时值仲夏,梧桐街张灯结彩,热闹非凡。名震天下的林家梅花枪第十二代传人林宁林提辖正在娶儿媳妇。 亲家公张天山原也是东京一个厉害角色,曾任大宋御林军的箭术教头,雄腰猿臂,百步穿杨,人称「小养由基」,但因年纪渐大,老眼昏花,体力下降,渐渐的不为朝廷所用。妻子早逝,膝下仅有一女相伴,名唤张霞,所幸从小聪明伶俐,善解人意,偏又长得体态窈窕,风姿袅娜,天生的一副美人胚子。 林宁与张天山都是同朝为大宋天子办事的,原也早就相识,一日两人在茶馆饮酒,林宁在担忧犬子林冲整天混迹瓦肆弄堂,不务正业,一味的使枪弄棒,好勇斗狠,颇有给他找个老婆之意。 言者无心,听者有意,张天山正是山穷水尽之时,度日维艰之际,再加上不得已的苦衷,就说了些「小女粗陋,恐有辱门风」之类的客套话,当下两人谈著就觉得投机,乘著酒意,就订下了这门亲事。 张霞静静地坐在洞房里,打扮得如春山妩媚,夫君林冲尚未进屋,想是在外招呼客人。 她悄悄揭开盖头,但见屋内陈设简洁,窗明几净,窗户上贴著几张大大的「喜」字,洋溢著喜庆的气氛。 她闭目沉浸在遐想之中,想起从此将与另一个陌生男人共度余生,不禁心下缱缱,她的思绪随著几案上的烛火袅袅飞扬…… 那年,张霞年方十四,正自蓓蕾初开,明眸皓齿,流丽动人。 记得好像也是在这样的一个夏日里,阳光明媚地透过屋外葡萄架的缝隙泻进了幽静的庭院,张霞躺在红木榻上沉睡著,身上穿著一件玉锦罗衫,映衬著雪白的肌肤,俏立的双乳隐约可见,香腮晕红如贵妃醉酒一般。 她的下身系著一条水红纱裙,一双三寸金莲斜挎在木榻靠手上,盈盈一握,活生生的可爱。 张天山正从教场上回来,热汗淋身,猛然看见女儿那幅海棠春睡图,久旷的心海顿时起了波澜。由於他整天忙於公事,家中事务常常让邻家的刘婶帮忙,女儿的日常起居又有小丫环锦儿照顾,却不曾想到女儿竟长得这般大了。 他呆立著看了半晌,欲火飞升,胯下的阳物高举,坚硬如石,只觉得唇焦舌燥,下腹高涨,尿意频频。 虽然他常常出没花街柳巷,但萤火怎与日月争辉,再出色的妓女也不如这如出水芙蓉般的娇艳。 他慢慢的跪了下来,轻轻地卸下那水红纱裙,掀起里面的小衣,但见圆鼓鼓的白白阴阜上覆盖著些许柔软的阴毛,阴牝肥大丰美,就如邻街王大娘家卖的面团似的丰润光泽。或许是天气炎热的缘故,她下体的肌肤显得潮湿,色如人乳,散发著淡淡的清香,如桃花绽放的小浪穴一开一合,彷佛婴儿之嘴嗷嗷待哺。 张天山终於抑制不住自己,颤抖著把那双充满老茧的手放在高高突起的阴阜上摩挲,触手处温暖细腻,光滑如缎。 就在此时,张霞「嘤咛」一声从梦中醒来,在睡梦中她感觉有风沙掠过,刮痛了她娇嫩的肌肤,可没想,一睁眼却看见父亲正赏玩著自己最隐秘的地方,她一时吓得呆了。 从小就经过「三从四德」教条的灌输下的她对於父亲的敬畏是根深蒂固的,她羞红了脸,怯怯地道:「爹,你在干嘛?」 此刻花影轻移,黄莺在葡萄架上清脆地啼鸣,那股处女的清香交杂著墙角传来的花香刺激著张天山的神经末梢。他欲火已然在心中燃烧,耳中哪能听得见女儿娇怯的声音,满眼尽是女儿那白里透红的脸蛋。 「好女儿,你莫叫,依了爹地,爹地什么都给你。」 他脱下她的上衣,粗糙的手已是捏住了那勃勃而立的乳头,仔细揉搓著,只觉得湿热润滑,心旌摇荡。张霞感到脸颊滚烫,如火燎一般,通体燥热,一张小嘴已是挤出几丝呻吟,嘴角轻翘,更是惹人怜爱。 「我要邻居小梅家的那种丝缎,还要余杭产的。」 那日见过小梅穿著一身绫罗,俏丽动人,张霞嘴上没说,心里却甚为妒忌,颇想也拥有这么一样。 张天山见女儿肤若凝脂,唇似涂朱,香乳挺立,迎风招摇,已是魂飞魄散,不知所以了。 「好、好女儿……爹地还给你买临安的宫花,金陵的玉镯……好霞儿,你真香!」 此时就算是天上的星星,他也要把它摘下来送给她了。他松开了双手,解开了腰间的丝带,脱下长衫与内衣,露出了还算壮健的胸膛,上面的黑毛密匝匝的甚是吓人,张霞心下狂跳,血冲脑门,急忙闭上了眼睛,但随即又微微眯著,却见父亲那话儿已是高高翘起,顶得内裤像是支起了帐篷。 张天山抱紧女儿,只觉心痒难搔,已是将一张胡子拉匝的嘴凑上与她相接,咂舌之声不绝於耳,张霞丁香暗吐,香涎甘甜芳菲,沁人肺腑。 张天山如身在云雾之中,神仙也不过如此而已!他一手抱著女儿的纤腰,一手抚摸她光洁的胸部,到处都是酥酥软软,触感舒服,他可以感觉到女儿已经渐渐动情。 在这情场老手的撩拨下,张霞春情难耐,胴体有如火练,轻声呻吟,如莺啼鹂鸣,嘤嘤咛咛,双手已是抱住父亲雄壮的腰身。 张天山的嘴移至女儿的胸部,吸吮著她那两颗紫红的樱桃,恨不得一口吃进肚内,他的舌头轻抵著乳头,只那么一下,就让张霞感到无比的麻酥,她一阵的抽搐。 张天山的一双枯手已伸进女儿的下身,隆起的阴阜有柔软的阴毛覆盖,触手之及,都让张霞不自禁的紧夹住双腿,脸如火烧,喘息声越来越大,丰腴的身体如蛇般扭动,显见得她的内心是骚动不已,她的手儿也伸过来抚摸著父亲那高昂挺立的话儿,只觉身在空中,轻盈如鸟,直欲飞去。 张天山分开她那修长曼妙的双腿,股间芳草离离,阴牝处光亮湿润,惹人爱怜,一脉清流正自从那销魂穴中渗出,色如人乳,香气熏人。 时当正午,树上知了乱鸣,张霞仰天躺著,两腿大大张开,粉脸娇艳,媚眼如丝,娇啼不断,小手纤纤的在小乳上不停地揉搓著。 张天山看到女儿那般的浪态,淫声不断,阳具已是蠢蠢欲动,他一手扶著已是挺将过去,龟头刚抵一半,只听张霞已是痛得大叫,「啊!!爹……女儿痛死了……女儿不要了……」 她的阴牝突然间被一个硬硬的东西塞进,顶得阴牝内奇痛麻辣,急忙伸手摁住了那根滚烫如火的阳具,「爹,我那里要裂了,我要死了……」 怎奈此刻张天山正在紧要的关头,岂有就此罢手之理,他已是猛然一掼,龟头尽入阴牝深处,直抵花心,张霞痛得珠泪翻滚,阴牝之内犹如刀绞般的疼痛难当,她浑身肌肉僵硬,贝齿紧紧咬著朱唇,屏住呼吸,「爹……可怜女儿蒲柳弱质……切莫再用力了……」 张天山听了不禁有些自责,忙放慢节奏,轻抽浅送,款款温柔,渐渐地只觉得里面滑腻非常,想是已入佳境。 他眉飞色舞地腰肢大摆,弯腰细细看著阴器相接处,见那阴牝饱满丰润,阴唇时开时阖,艳若桃花,阴毛上沾染了几许处女血,鲜艳夺目,映照著白白的阴牝,更显得奇诡无比。 处女奇紧的阴壁夹得他的阳具舒畅欢美,快感自小腹丹田传到顶门玉枕,再回流至阳具,他双眼紧闭,只管用力抽送,越来越快。 张霞初时疼痛,到了中途已是转为酸麻,她逐渐把持不住自己的矜持,放出了百倍的风情,粉臀轻抬轻放,体会那话儿在阴牝内的点、吮、抵、啄,真如青蛇吐信,咬得她是云鬓篷松,凤目斜睨,端的是奇淫风骚。 二人插送相接数百下,张天山老迈之躯渐渐不行,只觉双腿软弱无力,遂轻声呼道:「女儿,我要出来了……」 阳物一阵收缩,一股浓冽的精液喷涌而出,有如湍流飞溅,射在花心深处溅起朵朵浪花,然后双手紧紧地抱著张霞的丰满娇艳的胴体倒在了红木榻上。 而张霞也随著那股热浪的流入而舒爽异常,雨散云消,两人搂抱在一起,交股叠肩,大汗淋漓。 自此以后,父女之间的情事自是层出不穷,乐此不疲。然而乐极生悲,张天山年迈体衰,怎耐得住这年华正茂的青春女子,几年下来,竟落得满身的疾病。 这才思想著要将女儿嫁将出去,否则这身臭皮囊未免会提早去见阎罗王。 张霞见窗外月影渐移,然而夫君林冲却犹未进洞房,她长叹一声,将身子斜倚在缎花被上,美目将闭未闭,一只小手托著香腮,显得风韵楚楚,丰腴的胴体焕发著无上的春意。 就在此时,已是醉醺醺的林冲已是撞开门扉,只见四对大红蜡烛燃得旺盛,那新人正躺在床上睡著,但见那柳眉斜飞入鬓,长长的睫毛掩映下的杏眼微闭,樱唇轻启,脖颈间白皙光洁,端的是一个美人儿。 饶是林冲素来不喜女色,也不免情动。 要知林冲为人豪爽尚侠,虽年已三旬,却至今未婚,为的就是天生的厌恶女子,反而对龙阳之事是如猫儿遇腥,苦逐不已。现今囿於父命难违,只好违心娶妻,还是磨磨蹭蹭的直到深夜才进洞房来。 但一见张霞之绝世风姿,登时淫兴大盛,只看得心旌摇荡,呼吸急促,他伸出手来轻轻地抚摸著那如粉琢玉雕的脸蛋,只觉滑腻非凡,「娘子,娘子……」 张霞一下子惊醒过来,只见眼前一个锦衣男子,豹头环眼,燕颔虎须,八尺长短的身材,显得昂藏英武,不禁心下甚喜。 要知以前女子不过门是不知道夫君的相貌的,待得一见林冲之神采,她一下子就神为之夺,羞得低下了头,一张小脸红若彩霞,水灵灵的大眼睛已是秋波荡漾,「夫君来了……」 千言万语也只在那一瞬之间,林冲已是轻舒猿臂,三两下就褪去了她一身的新娘装,露出光晃晃亮晶晶的身子来,但见双乳尖挺,玉润珠圆,小腹平坦,双股之间芳草萋萋,玉唇儿张缩不已,显是情切切意真真。 他贪婪地看著这肥美丰腴的可人儿,颤抖著双手脱去了长衫,露出强健的肌肉,在呼吸之间更是鼓成块块,雄壮英武。 「也不知那话儿怎么样?」 张霞羞羞地闭上了眼睛,这新婚之夜可不能显得太过张扬,以免露馅,这是临行前父亲一再叮嘱的。她只感觉到,有坚硬的胡子渣正扎著自己娇嫩的粉肉,一根长长而潮湿的舌头正蜿蜒地往来於双峰之间,在这吸咂时她只有强自忍住直欲喷发的热情,全身香汗淋漓,娇喘不已。 「贱妾弱质,还请相公珍重……」 她纤手一摸,竟触到了一根又粗又长的滚烫之物,小手儿颤颤,「这物这么长大,贱妾好怕……」 娇啼婉转,显出不胜凉风的娇羞,林冲微微一笑,「娘子莫怕,林冲自当小心。」 他摇了几下亮晃晃的长枪,阴茎上青筋暴露,他将张霞抱起,自己跪在了床上,而张霞的两只纤手环环绕於他的脖子上,双腿自然而然的勾搭在他的腰间,林冲双手托著她的肥臀,把那阳物缓缓地送入了那销魂窟里。 张霞大痛,忍不住叫喊著,「疼,相公轻点……」 虽然已非处女,但林冲阳物之巨大实非其父能比,登时将她的阴牝拓宽,在里面横冲直撞,势不可当,不一会儿,就见阴道口流下些许血丝。 「好娘子,试试你相公的林家枪法吧。」 当下已如狂风骤雨般的一阵猛攻,那阳物时常连根尽没,阴囊在外不时的挤压在阴蒂之上,那张霞已是体酥声弱,欲仙欲死,好似身上的每一根骨头都被拆散一般。 林冲狂抽了数千下,将那话儿退了出来。只见张霞气喘吁吁的,全身香汗淋漓,已是被他弄得死去活来,瘫倒在床上,白生生的胴体刺激著林冲犹未退去的神经。 只见她两股之间茵茵绿草下一道峡谷豁然洞开,光光肥肥的阴户内有阴蒂高翘,如鸡冠微吐,似蓓蕾初绽。两片阴唇分开,四周淫水四溅,显是经过一番搏斗,张霞先自泄了。 他触手一摸,那淫水粘稠,如蚕丝连绵滑润,带得满手都是。 他轻轻一笑,翻转她的身子,吐出一口唾液涂在她的后庭,沿著菊花蕾边圈了几下,张霞只觉得奇痒难当,「夫君,你是要……」 她心下大惧,以林冲阳具之粗大,要插入那小小的缝隙之中,肯定是要死的了,她惊道:「不、不……」 可没等她说完,那根奇大无比的阳物已是生生的插入了她的肛门内,一股火辣辣的巨痛从后庭传来,她大叫一声,已是昏迷过去。 恍恍惚惚之中只感觉有一根铁锯在直肠内拉锯著,刮得内壁奇疼,慢慢的又转为酥麻,紧接著,有津液产生,润滑著那阳物的穿插,美妙的感觉霍然生起,她的双目不再茫然,放出了兴奋的光芒,尽管身下早已一片狼籍。 林冲由於久练武功,甚有长力,直插了再近千下,仍是犹有余力,抽插之间分外热情。 张霞只觉得后庭内如针刺般疼痛,直欲撕裂,已是鲜血模糊,血淋淋一片,惨不忍睹。 张霞不禁哀求著,「相公,不要再折煞贱妾了,贱妾快要死了……」 「那好吧,我再插下前面的吧。」 他把阳物提拔出来,复又插入了那牝穴内,双手抚著那弹性十足的丰肥屁股不断发力,直抵得她双乳乱甩,如醉如痴,牝穴内洪峰涌现。 林冲再一阵的猛烈进攻,才将积蓄已久的精液尽数送入了那牝穴里,只激得张霞哆嗦不已,飘飘欲仙。 一时间鲛蛸账中花残月缺,粉褪蜂黄,腥红涓涓,燕语喃喃。 第二回泄淫欲老林宁扒灰感亲情小张霞乱伦 次日早晨,林冲夫妇依例到前堂给父亲请安递茶,两人激战整夜,林冲身强体健倒没什么,却苦了张霞娇弱之躯,犹自下体疼痛,行走不便,蹙眉之际显得更是标致可人,饶是林宁原已不波的老井也起了些许微澜。 「你们下去吧,霞儿身体不好,你要多疼疼她。」 林冲诺诺连声,带著张霞回到内室,免不了又是一番行云布雨,共效于飞。 林宁虽老,但多年习武,虎老雄威仍在,当下看见儿媳妇妖娆无比,体下阳物勃然而起。 正思想著该如何是好,一个穿著淡绿裙子的小女子端著茶叶进来了,却是随嫁侍女锦儿。 且说这锦儿,年方二八,正在春心勃发之时,生得姿容清雅,因未经破身,自有一番少女风致。 「老爷,请用茶。」 声音清脆悦耳,然听在林宁耳中却不啻晴天霹雳,他一把将锦儿抱在怀里,老手轻狂,已是伸进她的裤裆内,把那牝户又摸又捏,霎时淫兴益浓。那锦儿下体猛然遭袭,不禁脸颊潮红,双手推却,「老爷,您莫这样……」 林宁已是心魂荡漾,难以自制,哪管弱女无力,双手连环,卸去锦儿的裤腰,露出雪白双股,恰似粉团一般。那牝户儿,红的红,白的白,阴蒂如鸡冠微吐,销魂小窍紧闭,显出一道小缝隙,煞是喜人。 锦儿虽常见张氏父女做那事,但毕竟那时年幼无知,目下年纪渐长,已是知晓人事。 当下被林老爷一番轻薄,难免情动,更想那销魂滋味却是如何让小姐欲仙欲死。 林宁欲火高涨,全身运劲一挣,衣物尽去,这「霸王卸甲」原是祖传功夫,也让他运用得娴熟无比。 锦儿怯生生的看著那勃然大物,长约七寸,只恐自家牝户狭窄,不堪重负。 然就在她犹豫之际,林宁已是抹些唾液在那阳物之上,凑著那光光肥肥的牝户儿一顶,仅进寸许,就听得锦儿痛哭出声,「老爷,可怜锦儿则个,要死了一般……」 林宁搂住锦儿粉白的脖颈,将那舌尖儿抵进她的小嘴,紧紧地吸咂著檀口丁香,体下阳物却是并不稍停,一连就是二十几抽,才得以尽数而没。 锦儿牝户如欲割裂般的痛楚,火辣辣般的疼痛,当下只是蹙蛾忍耐,直至林宁数百抽后,才苦尽甘来,婉转娇啼。 林宁只觉那牝户内阵阵紧缩,就如有一只小手儿轻握,湿润滑腻,不觉得又是狂抽乱送。锦儿也是呻吟声不绝,小手紧紧扣著林宁的双肩,生生划出几道血红。 林宁站稳马步,身似弯弓,臀部发力,一根阳具在里面拱进拱出,伸缩不定,龟头抵在花心深处,就如鸡啄一般快活。 锦儿的花心就像要开放了,昏去又醒,浑身乏力,却又快美无比,终晓得小姐为何沉缅此中之故了。 「好锦儿,似你这般妙物,缘何你家老爷不曾碰你?」 林宁边抽边问,他素来知晓张天山的禀性,岂容美物错过。 锦儿心魂俱散,只觉全身舒服畅意,不觉翘起秀美双腿缠在林宁腰间,气喘吁吁的道:「老爷,你不知道,我家老爷怎么会看上我,他与我家小姐早就…」说到此处,锦儿忽感不妥,忙闭上了嘴,只是唇间依然是呻吟不已。 那林宁老奸巨滑,一点即透,登时明了,腰肢用力,心下大骂,张天山这老东西,不是人! 林冲夫妻新婚燕尔,欢好月余,林冲的热情却渐渐显得有些淡了。 这日张天山兴冲冲的前来报讯,「东京殿帅府要招考八十万禁军枪棒教头,三日后在西郊校武场公开比武,冲儿枪法了得,可以去试一试,也好图个功名,封妻荫子。」 林宁也点头赞许,「对,学成好武艺,卖与帝王家,冲儿,你就去吧。」 林冲原也打算博个功名,好光宗耀祖,既然父亲吩咐下来,也是兴致勃勃。 是夜,正逢十五,月亮圆圆地挂在树梢头,林冲出外会友未归。张霞闲极无聊,走到中院纳凉赏月,她披著一件蝉翼薄纱,不施粉黛,淡雅清新,显得丰姿绰约。 就在她呆立沉思之时,传来一声「嗯哼」的咳嗽,她急忙回头一看,却是公公林宁站在身后。 「深夜风大,你穿这么少,可莫著凉了。」 林宁的声调平缓温柔,充满爱怜之意。 「公公,不会的,今儿个天热,我出来吹吹风。您还没休息?」 公公平日严肃,不苟言语,想不到却这般的体贴,她忙紧了紧身上的纱巾,公公的眼睛在暗夜里显得精光闪闪,奕奕有神。 其实林宁站在她的身后已是许久,这平静的小家庭里原本都是男人,自来了这个温柔美丽的儿媳妇后,他再也按捺不住潮涌的激情,经常悄立儿子的窗下,聆听他们做爱交媾的声音,然后回去自个儿在被窝里施展五爪功,安慰老去的情怀。 「没有,我睡不著……霞儿,冲儿对你好不?」 林宁凑上前去,已是一把抓紧了她的小手,纤手滑润细腻,鼻间有一股淡淡的清香,想是从儿媳身上传来的,他心中荡漾,吞下一口唾沫,胯下阳物跃跃欲试,真是欲罢不能。 「啊,公公……」张霞被公公的举动惊呆了,螓首低垂,小脸晕红似火烧,「大哥对我很好……」 只是这句话含在嘴里,嗯嗯哼哼的已是发不出声。 「好霞儿,你真是漂亮,公公第一眼看见你就喜欢你。」 林宁就著这夜色静美已是一把抱起了那曼妙的胴体,温暖在握,实是心魂俱散。 「不,不……公公,这不好,大哥就要回来了……」未等她说完,小嘴已被林宁的嘴封住,长舌一渡,顶著她的丁香就吸咂起来。 「霞儿,冲儿的功夫比你老父亲的如何?」 「啊,公公,您怎么……」 此时张霞一听之下已是魂飞魄散,一时间吓得也是全身酥软,任凭公公将她抱至他的屋内。 林宁把她放在榻上,轻轻脱去她的薄纱,但见玲珑剔透的胴体上凹凸分明,肌肤白若凝脂,如冰如玉般的晶莹,只看得他是心跳加速,呼吸急促。 林宁轻轻弹了下她娇嫩的乳头,然后低下头来细细的吮吸,这少妇的体香夹著乳香著实让他舒服畅快。 张霞被他这口中一含一放,一吸一吮,一种无边的快感随之即来,芳心可可,如欲仙去,她闭上眼睛,静静体会其中的滋味。 林宁在玩弄儿媳的乳头时,手指也未闲著,张霞的衬裤也是被他剥个精光,修长白嫩的玉腿横陈於公公的眼前,两股之间的秘处芳草离离,嫩红细白之物隐约可见。 林宁把她的一条腿儿抱了起来,低头轻轻吻著那桃花源处,手指的捻动叫张霞好生酥麻,不由得发出呻吟之声。林宁三下五下除去自己的衣衫,胯下阳物也是昂扬愤怒,凛凛生威。 张霞羞红著脸,低低的呼道:「不……这不行的……」 「好霞儿,你就顺著老爹一回……让你见识一下老爹的功夫,要知道林家枪法绝不比你老父的差。」 林宁迫不及待地分开她的两条腿,用手扶著坚硬如铁的阳具伸进了那紧紧密密的销魂洞里,当下已是抽送不停。 张霞的阴牝被插得满满的没有一丝缝隙,每抽拉一下,阴牝处的嫩肉便或进或出,明明灭灭,煞是惹目。她柳腰款款,粉臀抬放,迎合著林宁的抽插,每一次都是那么的一往直前,一捅到底,令她芳心灿烂,在这轻抽浅送之间淫语浪声不绝於室。 林宁抖搂著精神,一口气抽插了数百下,气喘吁吁的已是满头大汗,可身下的张霞淫兴正浓,「好公公,你要插紧一些,快插……」 浪语淫縻令林宁不知疲倦,只管埋头耕耘,奋力抽送,又抽了数百下,他下腹一紧,一股精液如离弦之箭一把把的射在张霞花心深处。 然而林宁虽泄,那小张霞却仍「啊啊」的乱叫,显然是还未尽兴,林宁低下头来,用手拨开阴牝处潮湿的浓荫,把那舌头伸了进去。 只见张霞浑身直颤,那紫亮的阴牝一收一缩的,而淫水便如春潮涌流,林宁张著大嘴把那些外泄的淫水一口一口的接纳,不时咂舌深吸,如饮甘醇。 ************ 果不出林宁所料,林冲在众多参赛的武士当中显得卓尔不群。 当见到儿子使出林家的看门绝招「梅花七出」把对手挑落马下时,他就知道现在的林冲已是青出於蓝而胜於蓝了,长江后浪推前浪,他不禁抚须赞赏。 经过这两天与儿媳的肉体鏖战,林宁倍感体虚,虽然在回春堂拿了些补药,但终无济於事,他能够感觉到自己的身子已是如江河日下,一日不如一日了。 但张霞那如火的胴体却又是那么的诱人,以致於他一次次的越轨,一次次的发泄著原始的能量,就在昨晚,张霞趁著林冲睡熟之际,还和他在厨房里的灶台上大战了数百回合,几乎要榨干了他,但他乐此不疲。 这一天,林提辖家中贺客盈门,都来祝贺林家公子林冲出任八十万禁军枪棒教头,来者多为京师武界名流。 其中还有林冲至交御林军金枪班教师徐宁,长得相貌堂堂,六尺五六身材,团团白脸,三牙细黑髭髯,腰雄膀阔,使得一手钩镰枪法,极是了得,两人由武相交而终成莫逆。 林氏父子杯来酒干,喝得痛快不已。张霞在内室也是高兴非常,毕竟夫君出色,她脸上增彩。 她细
最受欢迎标签